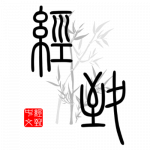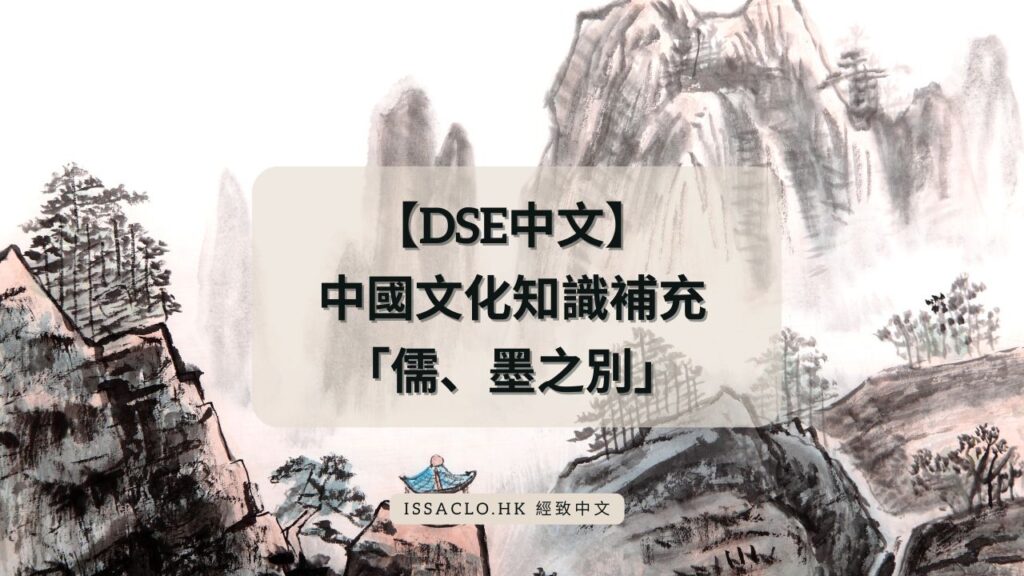在香港學習中文,學生對儒家思想可謂耳熟能詳。無論是閱讀卷中的經典選段,或是寫作卷中的名言引用,儒家的理念在書本筆記上總是佔據一席之地。然而,當我們談及「諸子百家」,你又對其他學派了解多少?是否只熟悉孔孟之道,卻對墨子、韓非等人一知半解?
本篇文章將聚焦於「墨家」與「儒家」兩大思想體系,從倫理觀、政治觀與經濟觀數個層面,結合不同經典篇章,比較二者在治國理念與社會經營上的分別。
一、儒、墨倫理觀
儒家:由親至疏,層層推展的「仁愛」
在儒家思想中,「仁」是最核心的道德觀念。孔子認為「仁」是一種能統攝各種美德的理想人格,而孟子則強調「惻隱之心,仁之端也」(《孟子‧公孫丑上》),指出仁心的起點,源於人對他人痛苦的不忍。從這種不忍見一人受苦的心,逐步擴展至關心家人、同胞、以至天下人,甚至愛惜動物與自然萬物,正好體現儒家主張的「由親及疏」的仁愛之道。
孔子亦曾對弟子曾子說過: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,謂之悖德;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,謂之悖禮」(《孝經‧聖治》),指出道德的培養必須從親近之人做起。這種由內到外、由近而遠的愛,既符合人之常情,亦與儒家的「禮」之觀念息息相關。孟子亦表達了相似的觀點,如「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」(《孟子‧梁惠王上》),以及「親親而仁民,仁民而愛物」(《孟子‧盡心上》),說明愛應從親人開始,再推己及人,直至普及萬物。
墨家:「兼愛」與「非攻」的平等倫理觀
與儒家「由親及疏」的愛不同,墨子則主張一種無分彼此、人人平等的「兼愛」。他認為,正是因為當時人們各自只顧私利、互不相愛,才導致家庭爭執、國與國互相攻伐,社會動盪不安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,墨子提出「兼愛」的主張,強調應一視同仁地對待他人,如同愛自己一般。他指出:「若使天下兼相愛,國與國不相攻,家與家不相亂,盜賊無有,君臣父子皆能孝慈,若此則天下治」(《墨子‧兼愛上》),意思是若人人實踐兼愛,社會便能和諧安定。
此外,墨子更將兼愛推展至國際層面,提倡「非攻」,即各國之間應互不侵犯。若能將對他國的態度視同己國,自然不會興兵作戰。墨子相信,只有摒棄私利、推行兼愛與非攻,天下才能真正實現太平。
一如《墨子‧兼愛上》(節錄)所言:
若使天下兼相愛,愛人若愛其身,猶有不孝者乎?視父兄與君若其身,惡施不孝?猶有不慈者乎?視弟子與臣若其身,惡施不慈?故不孝不慈亡有。猶有盜賊乎?故視人之室若其室,誰竊?視人身若其身,誰賊?故盜賊亡有。猶有大夫之相亂家,諸侯之相攻國者乎?視人家若其家,誰亂?視人國若其國,誰攻?故大夫之相亂家,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。
語譯:假若天下人都能彼此相愛,愛別人如同愛自己,還會有不孝的人嗎?視父親、兄長和君主如同自己,怎麼會做出不孝的事呢?還有不慈愛的人嗎?視弟弟、兒子和臣下如同自己,怎麼會做出不慈的事呢?所以沒有不孝不慈。還有盜賊嗎?視別人的家如同自己的家,誰會盜竊?視別人如同自己,誰會傷害他人?所以沒有盜賊。還有大夫互相侵擾家族,諸侯互相攻伐嗎?視別人的家族如同自己的家族,誰會侵擾?視別人的國如同自己的國,誰會攻伐?所以沒有大夫互相侵擾家族,諸侯互相攻伐。
從墨子的觀點來看,「兼愛」不僅是倫理層面的理想,更是一種治國安民的具體手段。他相信,若天下人都能真誠地彼此相愛,不分親疏貴賤,社會將實現以下三項穩定成果:其一,人民之間無爭無盜,民間自然安寧;其二,統治階層不再為私利作亂,政局趨於穩定;其三,國與國之間互不侵犯,世界得享和平。
這種設想看似理想化,卻不無道理。在現實社會中,許多衝突的根源正是源於自利與排他,例如家庭糾紛、社會不公,乃至國際間的戰爭,往往來自於「我群」與「他群」的分界心態。墨子的兼愛,正好對應這一問題。他主張「視人之國若己國,視人之家若己家,視人之身若己身」,嘗試透過放下界線,化解對立,構建一個整體互信的社會。
二、儒、墨的政治觀
墨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張「非攻」,強調一切形式的戰爭皆應加以譴責。他認為,戰爭無論是否出於正義之名,最終都會導致生靈塗炭、民生受損,因此應全面禁止。儒家則不盡相同。雖然儒家也反對濫發戰事,尤其是侵略他國的行為,但對於有明確道德正當性的「義戰」,如討伐暴政,則持贊同態度。
孟子便曾評論商朝末代君王紂王被誅殺一事,認為這是懲罰暴君的正義行動,而非弒君之舉:「聞誅一夫紂矣,未聞弒君也」(《孟子‧梁惠王下》)。這番話反映出儒家重視民心與正義,認為凡能解民於倒懸、為百姓謀福的戰事,亦可視為正當之舉。相比之下,墨子則認為戰爭必定「奪民之用,廢民之利」(《墨子‧非攻中》),即使是所謂的義戰,也逃不過勞民傷財的本質,因此予以嚴厲反對。
一如《墨子‧公輸》一文中,便能看出墨子的非攻觀念:
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,成,將以攻宋。子墨子聞之,起於齊,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,見公輸盤。公輸盤曰:「夫子何命焉為?」子墨子曰:「北方有侮臣,願藉子殺之。」公輸盤不說。子墨子曰:「請獻十金。」公輸盤曰:「吾義固不殺人。」子墨子起,再拜曰:「請說之。吾從北方聞子為梯,將以攻宋。宋何罪之有?荊國有餘於地,而不足於民。殺所不足,而爭所有餘,不可謂智;宋無罪而攻之,不可謂仁;知而不爭,不可為忠;爭而不得,不可謂強;義不殺少而殺眾,不可謂知類。」公輸盤服。
語譯:公輸盤為楚國製造雲梯的機械,完成後,將用來攻打宋國。墨子聽說了,就從齊國起行,步行了十天十夜去到郢,見公輸盤。公輸盤說:「你有甚麼指教呢?」墨子說:「北方有人欺侮我,希望借助你殺了他。」公輸盤感到不高興。墨子說:「我願意向你獻上十鎰黃金。」公輸盤說:「我不會違背仁義而殺人。」墨子站起來,再對公輸盤行了拜禮,說:「請讓我談談義。我在北方聽說你製造雲梯,將用來攻打宋國。宋國有甚麼罪呢?楚國有多餘的土地,而人口卻不足。犧牲不足的人口,去掠奪有餘的土地,不能說是有智慧;宋國沒有罪卻攻伐它,不能說是仁;知道這事而不去爭辯,不能稱為忠;爭辯而沒有成果,不能說是強;你奉行義而不去殺一個人,卻去殺害眾多百姓,不能說是明智之輩。」公輸盤被說服了。
在〈公輸〉一文中,墨子前往拜訪著名工匠公輸盤,其實是為了勸阻他替楚國設計雲梯攻打宋國。當時楚國意圖發動戰爭,而公輸盤製造的雲梯將成為攻城的重要武器。墨子得知此事後,認為此舉不義,遂親身勸說,試圖挽救即將面臨戰火的宋國。
在與公輸盤對話時,墨子故意提出一個荒謬的請求,表示自己想殺死那些欺負自己的人,並請求公輸盤幫忙。此言一出,公輸盤立刻表現出不悅,並斷言自己不會做出違背仁義的行為。墨子正是藉此設下圈套,引導公輸盤自己說出「不能違仁義」,再指出他若協助楚國攻打無辜的宋國,正是與其所言的「仁義」背道而馳。這種語言上的反諷與邏輯推理,不但展現了墨子辯才無礙的一面,也反映出他極力反戰的立場。
從這段引文可見,墨子一貫主張「非攻」,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。他指出,楚國疆土廣闊,資源豐富,根本無需侵略他國;而宋國亦無犯錯,不應無端遭受兵災。在墨子的眼中,戰爭會造成民生困苦,亦是對仁義與道德的踐踏,因此必須竭力避免。他不單以理說服,亦從道義出發,試圖令公輸盤自省,最終達致止戰的目的。
除了「非攻」,墨子還提出「尚賢」與「尚同」兩項重要政治理念。「尚賢」主張打破世襲與門第觀念,推崇唯才是用,不問出身,讓真正有能力、有德行者得以任政。他認為「官無常貴,民無終賤」(《墨子‧尚賢上》),即官位不應由身份決定,平民也有機會上位,只要其才德足以勝任。這一觀點背後,延續了墨家「兼愛」的平等精神。與此不同,儒家講求「正名」,主張社會中各階層應各安其位、各司其職。孔子認為名分有別乃社會秩序的根基,強調每個人按照其身分行事,社會方能和諧。
至於「尚同」,則是墨子對統一思想的另一種構想。他認為,社會中的人民應與上級保持一致,而君主的意志又須符合天意,這樣一來,才能消除混亂與爭端,達致穩定的政局。在他看來,思想越是分歧,社會越容易產生動盪,因此強調從上而下的思想統一。
三、儒、墨的經濟觀
除了批評儒家提出的親疏有別的愛,墨子亦對儒家重視的「禮」表示反對。他認為繁瑣的禮制不但令人民煩擾,更容易造成資源浪費,徒增百姓負擔。如《淮南子‧要略》記載:「以其禮煩擾而不說,厚葬靡財而困民」,正反映墨子對儒家禮制的批判,其出發點乃基於經濟實用的考量。
墨子強調「節用」,提倡節儉務實的生活方式。當時社會貧富懸殊,貴族階層生活奢華,與下層百姓的艱困形成強烈對比。面對此情況,墨子認為人的消費應以維生為本,凡不必要的開支皆應減省。因此,他反對儒家推崇的禮樂制度,認為貴族舉辦盛大祭祀、奏樂、宴饗,都是耗費民力、勞民傷財之舉,主張實施「非禮」、「非樂」政策。
此外,墨子對喪葬制度亦有獨到見解。他提出「節葬」的主張,反對儒家厚葬久喪的做法。儒家認為子女應為父母守喪三年,以示孝心,但墨子則從經濟角度出發,認為長期守喪會拖慢生產、妨礙勞動,對社會整體發展不利。
如同《墨子‧節葬下》節錄:
處喪之法,將奈何哉?曰哭泣不秩聲翁,縗絰垂涕,處倚廬,寢苫枕塊,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,薄衣而為寒,使面目陷陬,顏色黧黑,耳目不聰明,手足不勁強,不可用也。又曰上士之操喪也,必扶而能起,杖而能行,以此共三年。若法若言,行若道,使王公大人行此,則必不能蚤朝晏退,聽獄治政;使士大夫行此,必不能治五官六府,辟草木,實倉廩;使農夫行此,則必不能蚤出夜入,耕稼樹藝。
語譯:守孝的方法,是怎樣的呢?是哭泣沒有一定的時候,聲音咽塞,披着孝服垂淚,住在守喪時的簡陋棚屋,睡在草墊,枕在土塊上,又相繼強忍着不吃東西令自己飢餓,穿單薄衣服令自己受凍,使面上瘦骨棱棱,面容黝黑,耳朵不聰敏、眼睛不明亮,手足不強勁,不能做事。又說:上層社會的人守喪,必須他人攙扶才能起來,拄着拐杖才能行走,以此方式生活三年。假若遵照這樣的言論,實行這樣的做法,如果王公大人依此而行,必定不能上早朝遲退,處理訟獄、政務;如果士大夫依此而行,必定不能治理五官六府、開墾草木,使倉庫糧食充實;如果農夫依此而行,必定不能早出晚歸,耕作種植。
墨子指出:「死則既以葬矣,生者必無久哭,而疾而從事,人為其所能,以交相利也」(《墨子‧節葬下》),意即死者安葬後,生者應盡快投入勞作,實現各自的價值,才能互惠互利,推動社會運行。墨子以「節用」與「節葬」為核心,主張務實而非形式,反對一切虛浮而耗費民力的制度,展現出其重民生、重效率的思想。
簡單而言,儒家與墨家分別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:一重人倫秩序,講求情理分際;一講實用效益,崇尚平等節制。兩者在倫理、政治與經濟觀念上的分歧,不僅反映古代思想的多元,也為我們今日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寶貴的比較視角。作為學生,我們不應只熟讀儒家經典,更應放眼諸子百家,培養更全面的文化視野與批判思維,方能在閱讀與寫作中靈活運用,舉一反三。
如對於初中中文、DSE中文有任何問題,如私人補習、網上補習等,或者想知道更多關於DSE的資訊,歡迎Follow「學博教育中心 Learn Smart Education」 Facebook page 和 IG,以及 Issac Lo 的 IG,入面有所有你想知道和你需要知道的DSE資訊,助你全力應戰DSE!